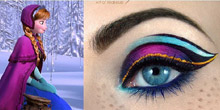◆ “与先人对话,向今人诉说。”牛国栋说,“我以私人化的叙述方式,以摄影和文字为双重表现形式,按照济南传统格局和街区大致走向,从老城中心启程,走到旧时的关厢,再到百年前的商埠,最后止于城郊山水之中。
牛国栋自嘲自己成了“胡同串子”。从泉城路到宝华街,从卫巷到官扎营,听说哪里要拆迁,他就拍到哪里,一边拍,一边听老人讲述老街故事。“济南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,许多老街老巷、历史建筑先后消失了,我心中的困惑也越来越强烈。”
□ 本报记者 王红军
济南,一座古城,四面秀色,半城湖水。但是伴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,数百条老街巷相继消失,大量历史信息不断消亡。于是,牛国栋再也坐不住了,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,他就拿着一台海鸥照相机,从一个市民的角度拍摄济南城和济南人的真实画面。
11月9日,著名城市学者牛国栋携其新作在泉城路新华书店签售,他最新的城市笔记《济水之南》,用24万字和200幅原创照片,让老济南回到过去。他说,“济南的文化传承香火不断,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,不必杞人忧天。”
从“练手”到“与先人对话”
十年前,牛国栋曾以一本《济南乎》风靡老济南文化圈。时隔十年的这本《济水之南》,不仅是《济南乎》的增订典藏版,而且再次唤醒了人们对老城老景的记忆。
牛国栋表示,“我对济南的理解和感悟是渐进的,涉猎自然也由窄到宽,由浅入深。《济水之南》的增订推出,绝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大幅增加,而是对济南历史文化作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和解读,主要的是对济南这座城市的关爱和呵护。”
祖孙四代生活在济南,这也不难理解牛国栋对这座城市的热爱。父亲曾在省博物馆工作的牛国栋,从小在广智院长大,英国传教士曾在这里建立中国早期博物馆,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省博物馆自然陈列室。童年的耳濡目染,对他的影响很深。
1987年,牛国栋有了一台海鸥4A相机。“刚开始就是‘练手’,从住的广智院等比较熟悉的场景进行拍摄,就是觉得好玩。”牛国栋表示,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自己开始对老城文化有意识地保护,不停地跟着街区走,拍摄济南和济南人的生活。
“与先人对话,向今人诉说。”牛国栋说,“我以私人化的叙述方式,以摄影和文字为双重表现形式,按照济南传统格局和街区大致走向,从老城中心启程,走到旧时的关厢,再到百年前的商埠,最后止于城郊山水之中。
拆到哪拍到哪的“胡同串子”
这些年,牛国栋一有空闲就扛起相机,步量济南的大街小巷,用镜头和文字把记忆中的故事记录下来。他表示,“老街老巷是一个城市的积累,每条街巷都有很多的故事。”
正是如此,牛国栋自嘲自己成了“胡同串子”。从泉城路到宝华街,从卫巷到官扎营,听说哪里要拆迁,他就拍到哪里,一边拍,一边听老人讲述老街故事。“济南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,许多老街老巷、历史建筑先后消失了,我心中的困惑也越来越强烈。”
牛国栋说,虽然自己不从事城市建筑和文化保护工作,但是作为一名热爱着济南的市民,感觉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东西留存下来。“于是,我就用相机和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并传承给后人,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和自觉的行为。”
在新作中,牛国栋将自己的亲历、专访、感悟、史料与原创摄影结合起来,从而使一座逝去的老城从纸面上呼之欲出。“济南作为一座数千年的老城,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儿受到他的滋润和颐养,这个城市发展可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,但我要通过这些文字和影像,还原这座老城优美的地方,把我们的乡愁和城市的记忆传承下去。”牛国栋说。
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
并不矛盾
“济南一直在行走。从数千年前的某一天出发,向着今天一步步走来,也要面向未来继续前行。”在《济水之南》的后记中,牛国栋这样写道。
跟着城市发展的步伐,牛国栋的脚步也没有停止。“我敲开一扇扇黑漆大门,去寻找和记录街巷内、四合院中和小洋楼里的历史证人。”牛国栋表示,自己采访的有时代居住在老街的“坐地户”,有老字号的传人,还有济南名门的后裔。
“在最多的一天,我曾经从泉城路一直走到宝华街,也就是现在的槐荫区。”牛国栋回忆说,“过去,很多人都说九华楼在县西巷,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座楼。于是,看到像样的房子,我就推门进去看,忽然看到一座楼的两个窗户像两只眼睛、大门像一张大嘴巴,走出来的盛先生说‘这就是九华楼’,名菜‘九转大肠’的诞生地……”
但是,牛国栋感到惋惜的是,一大批老街巷消亡了,一些老字号异地重建。“经济发展、城市发展不应该跟传统文化产生矛盾,这个矛盾有时候是人为的。”牛国栋呼吁说,“由于我们在拆除和保护时,大而化之地框定了一个范围,容易造成谁有钱谁说了算,这时候政府就应该站出来,把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,这也是城市管理者应该做到的。”
牛国栋感慨说,“这就像家里有很多古董,但非要把古董扔掉、砸掉后,再去买新家具装修吗?现在,大家已经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些问题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