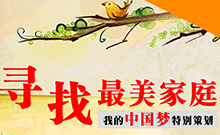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,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,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等,提振了种粮大户的信心。目前,我省各地都已开始春耕生产,种粮大户却面临着资金、灌溉、市场风险等种种难题……
□ 本报记者 孙亚飞 王兆锋
本报通讯员 张 波
高唐县尹集镇徐官屯村的侯廷涛,本是做农机销售生意的,去年流转了500亩土地,并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。
“经过一年试验,才发现种粮大户挣钱并不容易。”4月26日,淅淅沥沥的春雨中,看着自己的500亩绿油油的麦田,侯廷涛有些失落,“流转土地之前,我在网上看到,国家奖励种粮大户230元/亩,但我流转的那一年,政策就变成了一次性奖励100元/亩,而我签订了15年的土地流转合同,每年每亩地才合6.6元,加上小麦补贴的125元/亩,这就是我目前每亩地能够拿到的所有奖补。我也算了一笔账,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水电等等加起来,每亩地支出954元,这还不包括每年我支出的雇工费及土地流转费用。”由于今年浇水稍迟了些,小麦可能无法达到预期产量,侯廷涛已经做好了赔钱的准备。
阳谷县闫楼镇姜庙村的李俊文流转了1035亩土地种粮。因为应用了小麦“一喷三防”、玉米“一增四改”、秸秆还田等新技术,其粮食单产较全县平均水平高出15%。既便如此,他也遇到了苦恼:“一冬天没降水,是有些旱了。由于农田水利建设跟不上,去年我的800亩大方,黄河水引不过来,打井取水来不及,成本也高,旱得厉害。我只好通过铺管子的方法,从好几里外的地方把水引过来,这样算下来,每亩地光浇灌就得花60多块钱,而以前每亩只需要10来块钱。”
“土地每年产出的利润虽然不高,但还算稳定,加上中央1号文件提出,鼓励和支持土地向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流转,这更给了这部分人希望。”高唐县农业局工作人员么传训说,“很多人想通过流转土地搞农业赚钱,但这个钱怎么赚?关键要看当事人的理念。以种植业为例,很多种粮大户往往选择单一品种,比如种小麦就全部种小麦,种苗木就全部种苗木。粮食效益低,但受国家保护,风险小;经济作物效益高,但风险大。如果选择粮食与经济作物搭配种植的栽培模式,可以避免一部分损失,甚至还能提高一定的收益。”
么传训告诉记者,因经营不善“落荒而逃”的种粮大户并不鲜见,很多是因为误解了国家的奖补政策。“想通过流转土地获得国家奖补资金的人比比皆是。但换个角度想,这些敢于流转土地的人,依靠什么资金支撑呢?就目前来看,他们依旧很难得到银行贷款。国家既然支持和鼓励大户发展,配套政策却没有明确且连贯地实施起来。这成为了当下种粮大户们面临的一潭‘死水’,如何有效激活这潭‘死水’,还要依靠配套政策的及时落实。”
么传训依旧以种粮大户为例:“保证种粮大户的利益,是值得考虑的问题。我觉得,既然鼓励和支持,那么相关配套政策可以选择进一步向大户倾斜,不要大户小户‘一刀切’。比如说,一个农民就种了4亩地,每亩地补助10元,那么一年也就40元,如果每亩地拿出2块钱给大户,大户补助12元,因大户土地基数大,这2块钱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大数目了。”
阳谷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丁祥祺,研究农村工作多年,他介绍:“种粮大户经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后,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市场风险。一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自然特点,如遇有灾害性天气或市场产品过剩,几乎必然亏损,规模越大,亏得越多。二是缺乏‘组织感’,即单体面对庞大的市场。种粮大户基本都是单兵作战,土地、农资、技术、劳务、产品、销售等等,事事操心,显得力不从心。业主因投资失败和市场变化等原因,不能及时兑现农民租金,农民流转收益存在风险。这将给流转双方生活带来很大影响。这些问题需要探索解决的办法。”
本稿件所含文字、图片和音视频资料,版权均属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·大众网所有,任何媒体、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,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原标题:种粮大户春耕时节盼“活水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