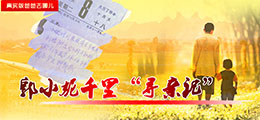各界委员再话治霾——成因不清 “心肺之患”无从根除
□ 本报记者 赵琳 魏然 江昊鹏
3月3日,北京城区又被雾霾笼罩。
下午两点多,人民大会堂门口,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像往年一样等候“围追堵截”委员。不同的是,很多记者戴上了专业防霾口罩,白色的口罩星星点点,分布在广场各处。
委员们一步入广场,在被追问“今年您最关注什么”时,多会微皱眉头,不约而同地回答“雾霾”。著名导演陈凯歌委员一抵达广场,没等记者开口,就用宏亮的声音大声说:“我最关心的是呼吸问题!”
谁都在呼吸这样的空气,谁又能不关心呢?记者近日遍访各界委员,他们给出了自己对雾霾的看法与对策。
不保护生态终究会被报复
研究生命科学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贺林委员,曾解出了“世纪之谜”——“A-1型短指(趾)症”病因。他从人口繁衍的角度对雾霾危害进行了分析。
“毫无疑问,雾霾对于人的体质肯定有影响。”贺林说,有些民间的课题组曾用小白鼠作过研究,吸入霾的小白鼠,肺癌的发生率大大增加了。北京地区也有过近年来肺癌发生率逐年递增的统计。“不难理解,新鲜的空气给人的身体带来好的影响,而雾霾则加重了身体的负担。”
贺林表示,虽然没有直接的科研证据证明雾霾与出生人口质量之间的联系,但是个人体质下降的民族,是无法保证后代繁衍的优良基因的。“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忧虑:不敬重自然,不保护生态,终究会被自然所报复。”
不能拍拍脑袋就作决策
空气质量差,很多人首先想到问责环保部门。而中国林科院森环森保所教授杨忠岐委员认为,环保部门责任固然很大,但雾霾凶猛,“板子”不能都打在环保部门身上,问题也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。“要让空气质量好起来,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肯定不能再发展了!”
济南市政协主席殷鲁谦委员认为,防治雾霾,最根本的是转方式、调结构,加快调整能源结构,淘汰落后产能,减少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。最直接的是采取行政手段,对违法违规的污染行为实行严惩重罚;实行区域联防联控,下达政府行政指令计划,实施政府目标责任考核;对污染企业实行限产限排,直至搬迁拆除;对特大城市机动车实行限行限购等等。
“可以调,可以罚,可以禁,可以限,但归根到底,是个政府决策问题。”贺林说,任何一个方案的出台,都需要有科学依据,不能拍拍脑袋就作决策。比如国家要开建一个工程,必须经过系统的科学论证,而不是找来所谓“专家”叫叫好就行了。
治霾须“对症下药”
一些委员认为,防治雾霾首先要搞清楚雾霾的主要来源,然后再对症下药。然而一些部门、地方政府过于急切满足“舆论呼声”,没有认真研究、系统梳理雾霾成因,导致治霾措施十分被动。
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车黎明委员告诉记者,“污染排放是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污染链条的最终端了,很多地方为了缓解舆论压力,在终端治理方面有较大动作,而对其他见效慢的措施则‘提不起兴趣’来。”
“科学治霾必须对症下药。”殷鲁谦说,目前机动车尾气排放对雾霾的贡献率,媒体有4%、22%、47%三种说法。到底哪个数字准确?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,科学治理雾霾无从谈起。“应该成立专门的雾霾研究机构,加强雾霾成因及治理研究。”
此外,殷鲁谦还建议治霾研究应突出地域性,比如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京津冀城市群、山东半岛城市群、中原经济区以及其他地区的雾霾成因各有差别,需要开展差异化研究,才能制定出科学有效的防霾方法。
(本报北京3月3日电)
本稿件所含文字、图片和音视频资料,版权均属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·大众网所有,任何媒体、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,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