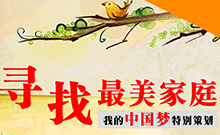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街道办开河社区
“农转非”遇社保盲区 老有所依成奢望

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街道办开河社区人迟迟拿不到社保。 □记者 鲍青 报道
□核心提示 上世纪80年代末开河村开始搞“旧村改造”,村民由“农民”身份转变为“市民”。在农转非的进程中,开河社区所剩无几的耕地被全部征用。开河人至今没有享受到征地补偿款,也没有获得就业安置,更没有办理社保。何以为生的难题一日不解决,开河人的烦恼便一天天不能拂去。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20多年前,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街道办开河社区的居民,由“农民”转变为“市民”。但随着岁月移转,开河人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承受生活的重担。在失去昔日生活来源且没有正式工作后,他们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,更因没有被纳入社保范围,生活变得愈发艰难。
尽快享受社会保障,是他们期盼能“老有所养,老有所依”的最大心愿。
“虎头蛇尾”的农转非
2月25日,记者乘车来到开河社区调查采访。开河社区的楼房修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,距今已有20多年历史,虽显陈旧却仍能一窥当年的风华。
据开河社区77岁的前任党支部书记刘可汉介绍,上世纪80年代末开河村开始搞“旧村改造”,村民由“农民”身份转变为“市民”。他告诉记者:“那个年代,因为全村人均耕地过少,而且靠近市区,淄川区开始对我村进行农转非,让我们整体上楼。”
在农转非的进程中,开河社区所剩无几的耕地被全部征用,不留“一厘一毫”。“大部分土地被征用搞建设,小部分作为储备用地允许农民暂时耕种。”开河人张绵华(化名)告诉记者:“现在淄川区的鲁泰体育场,烈士陵园还有一些学校,都是占的我们村的地。”
没有了耕地,也就意味着开河社区居民失去了赖以谋生的收入来源。刘可汉回忆,多年前,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蔬菜大棚,靠蔬菜种植为生,生活颇为富足。“从前我们村种蔬菜,供应淄川市区,生活挺滋润的。”在老开河人口中,仍喜欢将开河社区称为“开河村”。在曾经富足生活的记忆中,还流传着“一座大棚培养一个大学生”的趣事。
刘可汉等人向记者透露,当时“农转非”,相关部门曾承诺过帮助解决村民工作、给予社会保障等。但在改造完成后,言犹在耳的承诺却成了虚幻。“当时征地很像政治任务,个人的利益都被牺牲了。”所以即使这些承诺没被兑现,部分村民也只得缄默无言。
令开河社区居民雪上加霜的是,储备地给予的部分补偿,一直放置在村委会这一层中,“从来没有分给居民,村民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。”
没有享受补偿款,也没有给予就业安置,更没有办理社保,开河社区的居民的命运从那一刻便注定,往后的生活将变得较为艰难。
“区政府旁的‘灯下黑’”
虽然开河社区部分人的生活较为艰难,但在外人看来,开河社区的位置却是得天独厚的“优越”。吴法增(化名)告诉记者,开河社区北门两边就是淄川区财政局和经信委,往西一里地是淄川区政府,是和政府“比邻而居”的好地段。
虽是地段好,开河人却难以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待遇。杜清运(化名)告诉记者,“我们不是农民了,不能靠土地养活自己。但没有正式工作,也享受不到市民的待遇,我们是‘夹心层’,夹在中间很辛苦。”刘可汉更是直接将开河社区,形容为淄川区政府门口的“灯下黑”。
刘可汉给记者举例子称,“现在周边好多村都在搞旧村改造,个人利益都得到了很大满足。不仅补偿款落实到户,村里每年还给发福利。”在面对“为什么越早改造越凄凉”的疑问时,他给出了“越早革命越悲惨”的答案。
开河人告诉记者,如今的开河社区面貌有了很大改善。2013年,为了配合创建“全国文明卫生城市”,般阳街道办出资将开河社区坑坑洼洼的主干道修葺一新,令开河人苦涩的心理难得欣慰了一回。另外,去年开河社区还完成了电路改造、暖气入户等民生工程。但这些利民工程的顺利实施,多数还是和政治大形势有关,不具有可持续性。刘可汉说:“要不是离区政府近,容易被上级检查,这破路还指不定哪年能修好。”“灯下黑”的优越性,难得有了一次体现。
但这些进步,对于开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。何以为生的难题一日不解决,开河人的烦恼便一天天不能拂去。
社保盲区,老有所依成奢望
在农转非工作完成后,从前仅有700多人的开河村,人口规模开始迅速膨胀,目前人口已经超过2000。“一些农村有钱有关系的,就落户到我们村,成为城区人,然后再解决工作问题。”开河社区30多栋楼房中,绝大多数住着新开河人。
对于老开河人而言,上楼的新鲜感消退后,生活的重担便接踵而来。刚改造时,村民还是年富力强的壮劳力,虽然没有被安置工作,靠着打工养家还是绰绰有余。但20多年后,这些壮劳力逐渐步入人生暮年,打工生活难以为继,生活顿入困窘。如何实现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?成为他们心中最大的疑虑。
老支书刘可汉和老伴苦心经营着一家小卖部,靠着卖点生活用品过活。不过,在记者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,却不见一位顾客上门。
村民杜希学形容枯槁,脸颊遍布褶皱,看起来比64岁的真实年纪苍老许多。他向记者透露,因为没有正式工作,没有缴纳社保,现在每月只能靠着给人家单位扫地谋生。更为不幸的是,“我还有病,不能天天去扫地,一月挣不了几个钱。”他和老伴都有慢性病,每月仅自己承担的医药费就有500多元。“前年在济南做了心脏搭桥手术,还欠人四五万块钱。”因病返贫,让杜希学的生活雪上加霜。
杜希学当年是响应计划生育的头一批,如今儿子要供养四位老人,生活压力颇大。他时常想:“要是当年能办个社保,能给孩子们减轻负担,现在也不用这么愁了。”与他想法相似的,开河社区的老人不在少数。
“老无所养”是开河社区的常态。最令老开河人痛心疾首的,却在于几位居民因贫穷而病死的往事。逝者张绵胜,平时在村里捡拾破烂为生,生活困顿,在好不容易办理低保两个月后,就溘然长逝。村民刘继生和儿子刘潘,也因为家贫导致疾病无法医治而去世。杜希学说:“他们两人生病的时候,村民还自发搞过募捐,但还是没留住人。”在杜希学看来,非致命疾病却还能要人命,家贫是至为关键的要素之一。他说:“就是平常没钱生活,才让疾病恶化的。”
杜清运问记者:“都说21世纪中国社会老龄化明显,那肯定有配套措施保障老人晚年生活,你说我们这样的能享受到吗?”
为何开河社区居民没有纳入社保范围?3月3日上午,记者以村民身份致电淄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,因为年代久远,农转非的相关政策已不清楚。
记者查阅了解到,北京大兴区部分农转非居民,与淄博市淄川区开河社区居民的情况相似。可大兴区政府已为征地农转非人员补缴了各种社保2亿多元,其中最早涉及到上世纪80年代农转非的居民。
本稿件所含文字、图片和音视频资料,版权均属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·大众网所有,任何媒体、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,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。